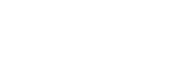《转租房子合同精选4篇》
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转租房子合同精选4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转租房子合同 篇1
转租方(以下简称甲方):_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
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双方就下列房屋的租赁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将坐落于的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转租(房屋的格局为_____室_____厅_____厨_____卫)。该房屋用途为生活用房。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任改变房屋用途。
2、甲方于3月8日与出租房季某签订半年租房合约,现转租给乙方。
3、甲方与乙方合约签订完之后房屋发生一切损失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与出租方自行解决。
4、乙方向甲方支付金额——元,
5、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该房屋毁损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6、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并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项,均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本合同连同附件共____页,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出租方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法定**人(签字):_________法定**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基督教诗歌 篇2
基督宗教在黔西北彝族中的传播与活动,对彝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基督宗教传人黔西北彝族之后,对信教民族群众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生活方式、卫生习惯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导致民族社会发生变迁。彝族文化是自成一体的文化,从天文历法到治国方略:从宗教信仰到诗词歌赋:从耕牧纺织到风情习俗,其包罗万象的构架,一直以自身强大的力量对抗着形形色色的文化冲击。在这些文化同化和文化征剿中,从来没有哪一种文化敲开过彝族文化的大门,有的反而被彝化。如明朝时从南京一带迁来黔西北的南京人(白族),说彝话,习彝俗,甚至用彝文写碑文,和彝族没什么两样。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基督教传教士却意外地使黔西北彝族陆续皈依了基督。如前所述,尽管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彝化,但无疑也使彝族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宗教信仰的变异
黔西北彝族的宗教信仰也同其他彝区彝族的宗教信仰一样,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集中表现为“万物有灵、自然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是祖先崇拜。对各种神灵的祭祀主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一核心。
彝族宗教信仰还表现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毕摩”和“苏业”。特别是“毕摩”。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还是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承担着与神沟通和教化人民的重任。他们通晓彝文,熟知天文、历法、谱系、伦理、史诗、神话传说及彝文文献,是人神之间的沟通者。但凡生死、年节、集会、灾病等都要请“毕摩”念经作法。布摩有卷帙浩繁的经书,分为祭祀经、占卜经、驱鬼经、招魂经、松魂经、指路经等几十类数百种。除经书外,毕摩还有神扇、法帽、法铃、签筒等法具。因此,毕摩在整个彝族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人黔西北彝族地区,客观上提高了一些彝族人的文化素质。但却支解了彝族传统的宗教信仰。彝族宗教信仰由原来的多神崇拜转为一神崇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彝族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把彝族传统宗教信仰视作封建迷信中的偶像崇拜。因此。他们中的所谓的“有识之士”便率领信徒砸毁自己祖先灵房,烧毁自己家谱。另外,他们本文由收集整理认为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是人类的始祖,只有他才能拯救人类。其他一切宗教的神灵皆是妖魔鬼怪。要皈依基督,就必须与其他一切信仰划清界限,这样,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方能得救。
其次。彝族基督徒认为只有信仰耶稣基督,死后方能升入天国。彝族原始宗教认为,人死后应该由布摩念指路经指引亡灵回归祖界与祖先团聚。但基督徒死后却由教会牧师长老率众祷告,祈求亡灵升入天国,永享安乐。同时,丧葬仪式也由唱诗祷告代替布摩念经指路,雄浑悲壮的铃铛舞场面一去不复,气氛倒土不洋。
二、婚俗节庆的变异
彝族号称歌舞民族,不管婚嫁还是节庆,都离不开歌舞,且场面颇为壮观。黔西北彝族的婚嫁更具特色,整个过程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但基督教传人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不再举行彝族传统婚嫁仪式,不拜对方祖先,不准唱酒礼歌,阿卖克(出嫁歌)。他们视传统节日为封建迷信,把圣诞节作为他们的节日。逢年过节,便所有人聚到教堂唱诗祷告,导致了本民族很多优秀文化的失传。在基督教彝区,除了几件偶尔穿在身上的服饰和夹杂着众多神的观点的语言外。彝族文化已荡然无存。
三、饮食习惯的变异
基督教传人彝区前,彝族在饮食方面没有过多的禁忌,而基督教传人后。彝族基督徒就无形中有了很多饮食禁忌。他们奉行基督教的宗旨,不吃牲血,不饮酒,星期天不杀生,非基督徒敬供祖先的物品他们认为是敬过魔鬼的,带有邪气,因此,不得食用。诸多的生活禁忌,给彝族基督徒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族群认同的变异
“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中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从这个理论出发,彝族共同体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皈依了基督教的黔西北部分彝族也认同自己的族属,但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传承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被迫彝化,而皈依了基督教的彝族却也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黔西北彝族中形成了独特的基督教彝族文化,这种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二元结合。它含有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大部分因素,又打上了彝族文化的诸多烙印。在基督教在彝区成蔓延之势的今天,这种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它的独立性。在人类起源上,彝族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是人类之始祖,是万民之神,但凡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对自己是笃弭和六祖的子孙的观念也渐渐淡化,抛弃自己家支的“诺溢”和“侯渎”,把家族乃至民族的起源归结为上帝的创造。他们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一个小团体,排斥非基督徒及其传统文化,否定彝族文化的巨大成就,阻止其子女与非基督徒子女的婚姻。因此,造成了彝族基督徒与非
基督徒之间的隔阂、抵触,甚者相互攻击、仇恨。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信仰基督教的彝族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彝族从宗教层面而论已经不是同一类人,反而对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却采取比较认同的观念。这种盲目的宗教观严重影响了彝族内部的团结。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但这种由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变异思想却使彝族族群认同的力量大大分散,彝族内部凝聚力大大削弱。
五、思想意识的变异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力量。它宣扬“信仰耶稣,死后会上天堂,不会下地域,来生不再吃苦受累”。受这样来世观念的影响,很多所谓虔诚的彝族基督徒便倾其所有,把一切财物捐献给教会,认为这样就可以在来世升入天堂获得幸福。另外。他们不外出打工、经商,认为凡是经商都是吃人害人,把大好时光用于参加礼拜。
六、音乐文化的变异
基督教诗歌 篇3
摘 要:《天真之歌》是英国诗人布莱克所写的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之一。布莱克在《天真之歌》中写出了天真的三个阶段,从蒙蔽中的天真转到美好愿望中的天真再到优美想象中的天真,这也是布莱克的思想的转变升华,契合了心灵与天堂之和谐。全文充分表现了宇宙和谐观,蕴含了人类自身的内在和谐,以及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和谐。
关键词:刍议;《天真之歌》;和谐观
威廉姆・布莱克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的浪漫派诗人和基督教徒,也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对想象出宗教的幻觉进行深刻的思考,开创了想象力在创作中的应用,启发了迪兰・托马斯、爱米莉迪金森以及阿尔蒂尔・兰波,忠实的记录了生活中的经历和感触,是最优秀的净化知觉的信徒之一,提供了人们所缺的但是浪漫主义所学要的某些艺术品质。国外对于布莱克的研究比较早,国内兴起的较晚,国内对于其研究主要是从《天真之歌》的主题、艺术手法、意象的运用等着手的,缺少思想的探究和升华。作为虔诚的信徒,它的作品的创作的源泉主要是在基督教的圣经想象出的,本文在解读诗歌的基础上,探究其所蕴含的基督教的和谐观。
一、《天真之歌》的解读
布莱克作为浪漫主义的先驱,是“黎明前孤独的声音,寂静时分的歌唱者”[1]。《天真之歌》是由19首小诗组成的,包括《序诗》、《黑小孩》、《升天节》等,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亚当的伊甸园相联系。《天真之歌》不仅是圣经的隐喻,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隐喻[2]。《天真之歌》的中心思想主要蕴含在《序诗》中,在这首小诗里,云端的孩子请求吹笛人为其吹奏一曲“小羊羔的歌”,并在听的过程中被感动,可谓是又哭又笑,并在最后流下了喜悦的泪滴。孩子在诗中央求吹笛人将其未尽之言写进书中,吹笛人则用一根空心芦管为每个孩子谱出动听的乐谱。文中吹笛人是被救赎后的圣徒,云端的孩子象征着基督耶稣,而吹笛人与上帝的孩子们同住,在人间建立天堂耶路撒冷,就像《马太福音》中所展现的那样人、自然、上帝的和谐统一,即伊甸园是一个隐喻,暗指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充满爱的和谐相处的状态。
《天真之歌》的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相契合的。中国的儒家思想讲究“中庸之道”即人类自身的主客观相和谐、“以和为贵”即人与人之间相和谐、“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和谐、“天人相通”人与宇宙、世界相和谐统一。而《天真之歌》之中的人与人、自然、上帝的和谐统一与儒家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天真之歌》中的和谐观
《天真之歌》中的和谐观主要是人类自身内在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3]。
1、人类自身内在的和谐
人贵在认识自己,就像曾子所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帮助别人谋略是否已经尽心,和朋友的交往是否已够诚心,是否已经复习所学的知识,儒家的思想就是认为人应重视内心的修养,寻找真我,保持真我,不为物喜,不以己忧。基督教的思想在这点与儒家学说相类似,强调自身的修养,就像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哲学的对象从来都是人的内心,即认识自己,保持真我,做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省,达到近乎于耶稣的神圣的气息,满足《哥林多前书》所写的基督教的要求“人应当自己省察自身”,强调人类自身的内在的修养和和谐。《创世纪》中的亚当和夏娃就是没有禁得住诱惑,迷失了本心进而偷食圣果,被赶出伊甸园,隐含着人类自身若是不重视自身的修炼的达到和谐,也会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升天节》中描写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一幕,即在升天节这一天每个孩子都穿着鲜艳的衣服在英国的圣保罗教堂唱歌的情景,孩子们受到了与往日不同的待遇,得到别人的尊重,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感谢上帝的慈爱和人们的好心。布莱尔在本篇诗歌中就强调人们应该互相尊重,摒弃身份、职业,愉快的生活在同一个天堂,遵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正如,儒家所坚持的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进而建设一个大同的社会。另外,《羔羊》、《对别人的悲伤》等诗歌中均体现了“爱人入己”的人与人的相处方式,强调建设人人相爱的人间天堂――耶路撒冷。
3、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儒家思想中,天就是自然,天道就是自然的运转。儒家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该“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督教的思想中也是这样的意思: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让人类生活在伊甸园中,与上帝同在。《天真之歌》中的《夜》、《春》、《笑歌》、《鲜花》和《保姆之歌》这五篇诗文就是给人们塑造一个人间的天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空”和一朵花儿关心并照顾着小雀,他们幸福欢快的生活着等,展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号召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再由人与自然的和谐翻沉人与人、人类自身的和谐,促进对于完善自身的追求。
结束语:
《天真之歌》以一首诗篇的形式,用精炼的语言和多种修饰手法,暗含丰富的人生的哲理,基于基督教的教义,描写理想中的世界,又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思想,强调人类自身内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张强,朱志勇。布莱克诗歌表现手法浅析[J].名作欣赏。2011,(06):35-37.
[2] 刘云雁,吴虹。威廉・布莱克诗歌的泛神主义倾向[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1):11-12.
基督教诗歌 篇4
[关键词] 民国;基督教;圣诗;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098―05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督教文学在民间一直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民国基督教文学的社会价值却多因其的超阶级性和乌托邦性而受到忽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为作家的基督教信仰所湮没。事实上,西方基督教信仰不但没有与作家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相抵触,其宣扬的那一套“平等、博爱”反而避免了爱国主义思想发展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社会的理性思维走向。
作为基督教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圣诗对基督教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圣诗通常出现于宗教场合,是基督徒为表示对神的赞美、崇拜或祈祷而作。自《圣经》诞生以来,大量圣诗随传教士的足迹跨越国界,传遍世界。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后,大批传教士携带基督教经典作品进入中国,为配合传教活动,众多中西基督徒合力编译了《普天颂赞》《团契圣歌集》《颂主诗歌》等数本圣诗集。这些圣诗以其内容上对神的赞美、对人的灵魂抚慰,及形式上对新诗的启发,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随着教会中中国信徒所占比重的日渐加大,教会及基督教文学作品的本土化特征也愈发明显起来。然而,中国基督教文人在改译、创作圣诗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往往因其宗教热情而受到以往研究成果的忽视。因此,本文欲藉重整中国圣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之机会,澄清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积极的社会意义,客观地重评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的社会价值。
一民国现实语境与圣诗选译标准
欲探寻民国时期圣诗中所蕴藉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需要回到其历史生成语境,分析此情此境中关于圣诗的选译标准,以从中窥见民国现实语境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其具体的圣诗选译行为的影响。
民国时期“政客弄权,祸国,党派私裂,贿赂公行。全国的同胞转徙沟壑之中。……国内军阀当道,杀气弥天,兵火所至,但见死亡相枕藉。……名为友邦,却趁乘我们的艰难,利用我们的颠苦,助长我们的内乱,借藉我们的愚鲁,运转我们的罪恶,来侵占我们的土地,攘攫我们的财源,鱼肉我们的同胞,剥削我们的,轻蔑我们的文化。”[1](p422)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有识之士深感拯救民族命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亦注意到了其所处时局与基督教诞生之初犹太民族的艰难境遇有着一定的可比性。众所周知,创立基督教的犹太民族千百年来饱受磨难,身负着命运重荷跋涉前行。上帝的存在、启示及救赎则是支持犹太人顽强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事实上,在赵紫宸、刘廷芳、杨荫浏等民国基督徒看来,犹太民族于苦难历史中凝结而成的基督教精神――坚忍、博爱、虔诚,正是此时中华民族所急需之品质,因此,他们身负十字架,开始了布道之路,坚守着“中华归主”和本色化教会的理想并竭力将之付诸实践,以期借助基督教文化为正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华民族重建民族信心,重整民族文化,继而真正解决本民族的现实问题。
选译圣诗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欲完成重整民族文化理想所迈出的第一步。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各族信众共创作了数十万首圣诗,以何为标准筛选圣诗经典并进行译介?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所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赵紫宸等人正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准筛选圣诗。反映世间民众之苦难处境以及上帝予以信众的援助,突出信仰于人之必要性成为该时期选译圣诗的主要表现主题。《平安歌》中,诗人将时世描绘为“邪恶尘寰”“尘事忙烦”“忧患交煎”“亲朋离散”“前途黑暗”,并一再重复着“如何能得平安?”(《普天颂赞》第二八七)的疑问。在这般绝望的生存环境中,被视为“救主”的上帝本着博爱的心向世界各族信徒伸出援助之手:或是以温情抚慰人心,赋予民众生存的信心,创作于危难之际的《灵友歌》道,“耶稣,我灵好友朋,容我奔投主怀中;洪涛暴雨冲我身,狂风卷浪高千寻;当此大难临头时,恳求拯救勿延迟;直到风静浪亦平,助我依旧向前行。”(《普天颂赞》第二八五);或是召唤信徒为生存而战斗,鼓励众人奔赴前线,在《信心基础歌》中,上帝道,“若遇烈火升腾,阻碍你行程,我赐你的恩,更广大,更丰盈!烈焰不伤你,却使你更真纯,消诸般渣滓”(《普天颂赞》第三四一)。这类圣诗所描绘之景状与民国社会的混乱状况极为相似,诗人所抒之忧虑也正与民国基督徒所思类同,后者正是借此以影射民国社会民不聊生之现实,而诗歌中呈现出的耶稣之视救赎世人为己任、信徒之乐观心态以及面对灾难时的坚强意志,则给予了身处混乱之世的中华民族信心和希望。
在早期的中国教会所使用的圣歌集中,由异族诗人创作、经由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转译为中文的圣歌占多数,但是,伴随着本色化运动的进展,中国基督徒逐渐开始在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信仰,朱维之、赵紫宸等人亦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不仅需要直译他国基督教文学作品,还应在翻译圣诗的过程中结合民国语境的现实需要进行再创作。
赵紫宸即译有《为国祷吁歌》(《团契圣歌集》第一三七):
一、世界威严之上帝,俯鉴我众忧惶,
悲我国家多艰难,百姓漂泊沦亡。
强邻虎视益眈眈,裂我锦绣山川;
求主振作我民心,使能抵抗强权。
二、求主拯救我民族,脱离残暴颠危,
脱离诳骗恶宣传,脱离龌龊行为。
保我国权与荣誉,使我努力警醒,
破除私斗崇公德,创造统一和平。
三、求主引导我中华,赦我罪孽重重,
拯我亿兆苦同胞,脱离水火之中。
鼓励男女众青年,使能力振颓风,
挽回狂澜于既倒,奠国基于无穷。
在这首诗的翻译中,赵紫宸不再仅限于文本的直译,而是对这首祈祷诗进行了再创作。诗歌前两节中,诗人向主祈福,迫切地期盼主能拯救处于忧惶艰难、“残暴颠危”中的国家民族,这是译者遵原作直译而成;第三节则是译者的创作,从原诗所描绘的苦难景象中,译者联想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因而发出“求主引导我中华”的祈祷,并在文末附上祷文:“大海翻涌,孤蓬一片,慈悲的父啊,求你救援中华,引导我们乘风破浪,安抵彼岸。我们载着五千年的历史,四万万的同胞,渡着险阻艰难的前路,神啊,保护我们。”由诗文可以看出,译者对于国家的命运无比担忧,在此,他将信仰的重要性置于亿万同胞眼前,期待主的庇佑和启示能引导“男女众青年”乃至中华民族走向光明。
由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文人为推广基督教信仰作出的努力。作为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整体推广至中华民族的媒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价值导向的作用,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译介工作,一方面有利于基督教文学在新环境中的被接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展出合传播者与接受者文学优势于一体的本土化基督教文学,因此,一定程度上的“误译”、“再创作”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译介主体的民国基督徒绝不仅是为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进程而选择将基督教本土化,借取基督教文化品格以满足本国社会及文学发展之现实需要,则是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因而,民国基督徒编写的圣诗集极具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对社会改良同样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主义立场与圣诗译作策略
如果说,民国的现实语境为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生成土壤,影响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选译圣诗的标准,那么,民国基督徒的民族主义立场则具体影响了其译作圣诗的本土化策略,并为其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实践空间。
正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所受到的质疑一般,近代以来,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最初是被赋予了一部分文化扩张的内涵。然而,承载着西方文化命脉的基督教事实上是一种有着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足力量的宗教实体。因此,维护民族自尊,立足于民族主义立场接受、传播基督教文化是中国教会人员从事传教工作的根本原则。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曾提出“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口号,为达到“自养、自治、自传”[2]的目的,民国基督徒在继承、发展西方圣诗传统的基础上亦注重圣诗的本土化改良,具体表现为采用适当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并创作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中国圣诗,以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丰富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传承注入新的生机。
为推动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民国基督徒做出了诸多卓越的贡献,在恪守中国语言文化传统惯式的基础上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即是其一。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格律美和节奏美,因此,为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圣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字词的斟酌、句式的对仗及节奏的和谐。他们多移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常用语词以及文体翻译圣诗,比如,将‘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译为“圣哉,圣哉,圣哉!全权的神明!”(《圣哉三一歌》,《普天颂赞》第一)译诗借用了“哉”这一文言语气助词,既渲染了情感的神圣,同时也实现了诗歌的韵律美。而文体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类:离骚体,如“耶稣纯美兮,超瑰奇与莹;生为神明兮为圣人,主我景仰兮,主我所崇尊,我心所宝兮逾奇珍”(《耶稣纯美歌》,《团契圣歌集》第三六);骈文体,如“上主之灵,恳求降临我心;默化我心,潜移俗念世情;垂怜卑弱,显主大力大能;使我爱主,尽力尽心尽性”(《上主之灵歌》,《普天颂赞》第六三);绝句体,如“虔诚奉献我全生,静候主命谨遵行;虔诚奉献我光阴,赞美歌声永不停”(《奉献全生歌》,《普天颂赞》第三一三),以及律诗体、长短句等等。这一特殊翻译策略的融入,使得这批外来圣诗经中文翻译后对仗严谨、格律严整,读来琅琅上口,易于传诵,从而推动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作品的传播。
与此同时,为真正实践其爱国主义理想,民国基督徒亦创作了大量中国圣诗以摆脱西方文化及思维惯式对于自身的束缚,并于本土化中国圣诗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宗教情感及民族期待,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中华民族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道德伦理,展现该类观念的文学作品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样,这一主题也是中国圣诗不可忽略的表现对象。《纪念祖先歌》道,“戴履兮,我藐躬,身体发肤何所从?抚躬自问,最难忘,水源木本,祖德宗功。抚养兮,父母恩,鞠育劬劳爱挚诚;午夜思维,最难耐,更残漏尽,月落黄昏。家训兮,历代传,铭心刻骨记真铨”。(《普天颂赞》第四三二)该诗取用楚辞体式记录了诗人对父母、祖先的感恩、缅怀。此外,《孝亲歌》(《普天颂赞》第四二六)亦言,“人生世上谁无双亲?父母俱存是福份;想念父母教养苦心,我生何敢负亲恩?父亲母亲当孝敬,上帝诫命当遵行;孝敬父母,遵诫命,成全神旨乐天伦。”该诗描述了双亲于子女,血缘于家庭之影响,继而将双亲与上帝并置,以突显家庭伦理与信仰于人之重要。由此,中华民族重血缘亲情、重孝道的民族性格可见一斑,而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延续使得民族文化传统得以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自基督教入华以来,中国基督徒文人一直保持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即在不损民族尊严的基础上接受基督教文化,同时,以借鉴为途径,以原创为目标,继承本民族风俗、文化成果,创作属于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归根结底,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即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直接呈现。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圣诗在此后各教会编纂的诸部圣诗集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且民族特色愈来愈鲜明,民国基督徒逐渐倾向于以圣诗这一异族文学体裁为形式,向其中注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他们对于民族自立和文学自尊理想的坚持影响了其民族化特色鲜明的译作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侵蚀,也促进了后者的良性调整和发展。同时,在中西文化交织、碰撞的复杂语境中,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亦可凸显出来,民族主义意识继而获得了稳固。
三爱国主义内涵与圣诗创作原则
由上得知,时势复杂的民国语境使得一群忧心于社会现实的基督徒赋予乌托邦的基督宗教以入世性,他们所坚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则推动了其完成圣诗本土化进而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进程。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对民族自尊的追求,都使得他们译作的圣诗中蕴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国基督徒看来,基督教文化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于中华民族有着启示作用。基督教集出世性与入世性于一体,一面提倡信众超然于尘世苦难的束缚,一面却关注信众在尘世中的生活。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品质是“爱”:爱己,爱人,爱民族国家。在圣经文学中,诗人担任着“先知”的角色,怀揣着“爱”的理想,将神旨传至世间,诗人大卫曾以诗歌的形式向耶和华呼求,“我的神啊!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常在我的心里。我要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福音;我必不禁止我的嘴唇”(《诗篇》40:8-9)。先知(诗人)的作用在民族苦难来临之时更显重要,他们承载着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奔走呼告;他们渴望涤清人类的罪恶,驱逐世间的磨难,挽狂澜于即倒,赋予人类生存的希望。
于民族患难中,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亦担负起了“先知”的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如果说,根据实际需要译介西方圣诗展现出一个民族在借鉴异族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那么,体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关键还是在于本民族作家的独立创作。出于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大批民国基督徒文人不但没有让自身的理性思维湮没于宗教热情或“学西方”的非理性热潮之中,反而积极投身社会,由“问题”出发,择取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化中相应的精神品质及问题的应对模式,以期有效地解决此时中华民族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怀揣着深沉的焦虑和担忧,诗人在《宣传福音歌》中叹道,“同胞呼救声殷殷……东起黄海浪潺潺,西渡云岭逾蜀山,北望广漠过榆关,南顾琼州到海湾,四万万人在水火,切望天惠早来颁;信徒岂可偷安闲,奋起救济时世艰。”(《普天颂赞》第二二二)在诗人充满焦虑的眼神中,广袤大地上的四万万同胞正在苦难中煎熬求生。关注社会现实,拯救民族与艰难时世,是肩负着先知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诗人的当务之急,也是其从事文学、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该时期大量来华西方人著述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民国基督徒在圣诗创作中还原了美好的中华民族形象,“历代迭生圣贤,功业裕后光前,感谢上帝保全,中华我国。地面宽洪辽阔,山川平原衍沃,中华美地;五谷百果俱陈,矿藏各种奇珍,众人均沾主恩,中华美地。”(《中华美地歌》,《普天颂赞》第二二九)即使此时的中华民族正为黑暗所笼罩,诗人仍能拨开阴霾,呈现出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圣贤辈出的美好中国。在这一美好的中国形象中,沉浸着诗人对祖国的热爱。正是出于这份深沉的爱,诗人感谢上帝向中国播撒福音种子,并祈祷中国能在主的福庇之下万世永昌。为中华祈福的同类诗歌占据了中国圣诗中的多数,另有许地山创作的《神佑中华歌》,“神明选择赐予,一片荆园棘地,我祖开辟;子孙继续努力,瘦瘠变成膏腴,使我衣食无亏,生活顺利。旧邦文化虽有,许多消灭已久,惟我独留;求神永远庇佑,赐我一切成就,使我永远享受平等自由。恳求加意护庇,天灾人患永离中华美地;民众乐业安居,到处生产丰裕,信仰、道德、智慧,向上不息。”(《普天颂赞》第二三)诗人向主展示了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星火相继、携手创造的“瘦瘠变成膏腴”的神话,并以此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护庇。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生了突变,自《马可波罗游记》起建构的神秘、富饶、乌托邦的中国形象认识传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大举入华而被强行打断,在《真正的中国佬》《变化中的中国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著作中,美丽富饶的东方帝国形象一去不复返,“落后闭塞”“保守自大”“懦弱愚昧”成为了这一代中国人的代名词,古老民族的自尊心严重受挫。因此,这批中国圣诗维护了中国的美好形象,对于亟待重建民族自信的中华民族极其重要。
此外,秉持着爱国主义信念的民国基督徒文人理性地区分了作为的基督教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推行基督教信仰的同时绝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的轻视和欺凌,他们秉着本色化基督教的信念,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基督教会势力的依赖,建立了独立的品格。同时,他们清醒地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发起了反抗,赵紫宸在该问题上鲜明地宣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教会革新的第一件事情,是扫除自己的房屋,廓清自己的圣殿,把粪秽肮脏一齐排弃出去。中国教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美国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完全地彻底地断绝关系。”[3](p220)以赵紫宸为代表的一群为实现“本色化”理想的民国基督徒一直以来都在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宗教实体严格区别于社会意识形态,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追随者亦截然不同于西方殖民势力的维护者。
忧国之危难,爱国之美好,盼国之复兴,基督徒文人与那些高举着社会革命或改良大旗的民国知识分子承载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只是选择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齐声高唱着“爱我中华民国”,称赞着祖国的“万里河山广漠,汉满蒙回藏族,共享平等幸福”,建构着“伟大事业造成,历史记载光明,友邦相慕相钦”的美好愿景,(《爱我中华》,《颂主诗歌》第二六八),虔诚地期盼以信仰的力量使世界走向大同,以此彻底扫除一切战争、犯罪、殖民主义等对纯净的心灵及和平的世界造成的侵害。面对着堪忧的现实及前途,诗人们仍旧充满信心地对归主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乌托邦式的构想:笃信基督,赎救罪孽,解放身心,友邻互助,归属基督教世界的中国社会也将重获光明。在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爱”这一品质的全新诠释。爱己,即爱国,关注个人及民族在尘世间的苦难处境,并以自己的身躯在黯淡无光的社会中探出一条通向光明之路,甚至牺牲自我以拯救喘息中的民族;爱人,即在自尊自重的基础上将爱由己及人,坚持民族独立性,坚决反抗一切触及本民族根本利益的帝国主义行为,理性鉴别外来文化中的不同成分,借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塑民族精神品格,重建民族信心,以使全族人民在这阵爱国主义浪潮的翻涌中齐心走出困境。
由此,不同于反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对民国基督徒的非议,即斥责其以基督教为政治工具宣扬西方文化,并借此殖民中国社会;或指责基督徒文学沉迷于精神而忽略现实……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那颗“爱耶稣爱中国的心”[4](p186),他们认为,“爱耶稣”和“爱中国”并不冲突,“爱中国”是因,“爱耶稣”是果,“爱耶稣”更是为实现他“振兴中华”的宏愿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他们关注现实,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以宣扬基督教义为手段,以信仰为力量,为中华民族设计了一条社会改良之路。他们亦相信,“中国人含蕴着伟大的创造力,要继绳祖武,在社会的组织,政治的结构,法律的规定,人生的意义上作一番自出心裁的创造。”[4](p186)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民族自尊不可抛弃,民族自信必须重建。同时,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反能避免爱国主义极端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万方团契歌》赞美道,“在主耶稣基督之中,不分南北西东;整个广大无边世界,契合在主爱中。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信主弟兄,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普天颂赞》第二四一)尊重各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独立性避免了“唯我独尊”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既提倡对民族文化的维护及发扬,以此建立起民族凝聚意识并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同时又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审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借鉴其文化精华以发展本族文化,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重整本民族精神体系。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开放而理性的文化视野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优化发展,对如何看待异质文化交流这一经久不衰的文化主题至今仍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紫宸。祷文(七)国庆日。祈向[A].赵紫宸文集・第四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2-423.
[2]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J].《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27.6-7.
[3]赵紫宸。中国教会革新中的自传问题[A].赵紫宸文集・第四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20-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