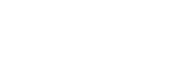《梁实秋的著名散文优秀2篇》
梁实秋经典散文《旅行》 篇1
我们中国人就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闹饥荒的时候都不肯轻易逃荒,宁愿在家乡吃青草啃树皮吞观音土,生怕离乡背井之后,在旅行中流为饿莩,失掉最后的权益─ —寿终正寝。至于席丰履厚的人更不愿轻举妄动,墙上挂一张图画,看看就可以当“卧游”,所谓“一动不如一静”。说穿了“太阳下没有新鲜事物”。号称山川形胜,还不就是几堆石头一汪子水?我记得做小学生的时候,郊外踏青,就是一桩心跳的事,多早就筹备,起个大早,排成队伍,擎着校旗,鼓乐前导,事后下星期还得作一篇《远足记》,才算功德圆满。旅行一次就是如此的庄严!我的外祖母,一生住在杭州城内,八十多岁,没有逛过一次西湖,最后总算去了一次,但就是自己不能行走,抬到了西湖,就没有再回来─—葬在湖边山上。
古人云,“一生能着几两屐?”这就是劝人及时行乐,莫怕多费几双鞋。但就是旅行果然就是一桩乐事吗?其中就是否含着有多少苦恼的成分呢?
出门要带行李,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就是旅行者的第一道难关。要捆得紧,要捆得俏,要四四方方,要见棱见角,与稀松露馅的大包袱要迥异其趣,这已经就不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所能胜任的了。关卡上偏有好奇人要打开看看,看完之后便很难得再复原。“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很多人在打完铺盖卷儿之后就觉得游兴已尽了。在某些国度里,旅行就是不需要携带铺盖的,好像凡就是有床的地方就有被褥、有被褥的地方就有随时洗换的被单,─—旅客可以无牵无挂,不必像蜗牛似的顶着安身的家伙走路。携带铺盖究竟还容易办得到,但就是没听说过带着床旅行的,天下的床很少没有臭虫设备的。我很怀疑一个人于整夜输血之后,第二天还有多少精神游山逛水。我有一个朋友发明了一种服装,按着他的头躯四肢的尺寸做了一件天衣无缝的睡衣,人钻在睡衣里面,只留眼前两个窟窿,和外界完全隔绝,─—只就是那样子有些像就是KKK,夜晚出来曾经几乎吓死一个人!
原始的交通工具,并不足为旅客之苦。我觉得“滑竿”“架子车”都比飞机有趣。“御风而行,泠然善也”,那就是神仙生涯。在尘世旅行,还就是以脚能着地为原则。我们要看朵朵的白云,但并不想在云隙里钻出钻进;我们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并不想把世界缩成假山石一般玩物似的来欣赏。我惋惜米尔顿所称述的中土有“挂帆之车”尚不曾坐过。交通工具之原始不就是病,病在于舟车之不易得,车夫舟子之不易缠,“衣帽自看”固不待言,还要提防青纱帐起。刘伶 “死便埋我”,也不就是准备横死。
旅行虽然夹杂着苦恼,究竟有很大的乐趣在。旅行就是一种逃避,─—逃避人间的丑恶。“大隐藏人海”,我们不就是大隐,在人海里藏不住。岂但人海里安不得身,在家园也不容易遁迹。成年的圈在四合房里,不必仰屋就要兴叹,成年的看着家里的那一张脸,不必牛衣也要对泣。家里面所能看见的那一块青天,只有那么一大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风明月,在家里都不能充分享用,要放风筝需要举着竹竿爬上房脊,要看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邻居没有遮拦。走在街上,熙熙攘攘,磕头碰脑的不就是人面兽,就就是可怜虫。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虽无勇气披发入山,至少为什么不带着一把牙刷捆起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呢?在旅行中,少不了风吹雨打,然后倦飞知还,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样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变成为暂时可以容忍的了。下次忍耐不住的时候,再出去旅行一次。如此的'折腾几回,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旅行中没有不感觉枯寂的,枯寂也就是一种趣味。哈兹利特Hszlitt主张在旅行时不要伴侣,因为:“如果你说路那边的一片豆田有股香味,你的伴侣也许闻不见。如果你指着远处的一件东西,你的伴侣也许就是近视的,还得戴上眼镜看。”一个不合意的伴侣,当然就是累赘。但就是人就是个奇怪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人陪着嫌闷。耳边嘈杂怕吵,整天咕嘟着嘴又怕口臭。旅行就是享受清福的时候,但就是也还想拉上个伴。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受得住孤独。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居多,避之唯恐或晚,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亲切的。到美国落矶山上旅行过的人告诉我,在山上若就是遇见另一个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脱帽招呼,寒喧一两句。这就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习惯。大概只有在旷野里我们才容易感觉到人与人就是属于一门一类的动物,平常我们太注意人与人的差别了。
真正理想的伴侣就是不易得的,客厅里的好朋友不见得即就是旅行的好伴侣,理想的伴侣须具备许多条件,不能太脏,如嵇叔夜“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太闷痒不能沐”,也不能有洁癣,什么东西都要用火酒揩,不能如泥塑木雕,如死鱼之不张嘴,也不能终日喋喋不休,整夜鼾声不已,不能油头滑脑,也不能蠢头呆脑,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晌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
梁实秋经典散文《旧》 篇2
“我爱一切旧的东西——老朋友,旧时代,旧习惯,古书,陈酿;而且我相信,陶乐赛,你一定也承认我一向就是很喜欢一位老妻。”这就是高尔斯密的名剧《委曲求全》中那位守旧的老头儿哈德卡索先生说的话。他的夫人陶乐赛听了这句话,心里有一点高兴,这风流的老头子还就是喜欢她,但就是也不就是没有一点愠意,因为这一句话的后半段说透了她的老。
这句话的前半段没有毛病,他个人有此癖好,干别人什么事?而且事实上有很多人颇具同感,也觉得一切东西都就是旧的好,除了朋友、时代、习惯、书、酒之外,有数不尽的事物都就是越老越古越旧越陈越好。所以有人把这半句名言用花体正楷字母抄了下来,装在玻璃框里,挂在墙上,那意思好像就是在向喜欢除旧布新的人挑战。
俗语说,“人不如故,衣不如新”。其实,衣着之类还就是旧的舒适。新装上身之后,东也不敢坐,西也不敢靠,战战兢兢。我看见过有人全神贯注在他的新西装裤管上的那一条直线,坐下之后第一桩事便就是用手在膝盖处提动几下,生恐膝部把他的笔直的裤管撑得变成了口袋。人生至此,还有什么趣味可说!看见过爱因斯坦的小照么?他总就是披着那一件敞着领口胸怀的松松大大的破夹克,上面少不了烟灰烧出的小洞,更不会没有一片片的汗斑油渍,但就是他在这件破旧衣裳遮盖之下优哉游哉的神游于太虚之表。
《世说新语》记载着:“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进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得故?’桓公大笑着之。”桓冲真就是好说话,他应该说,“有旧衣可着,何用新为?”也许他就是为了保持阃内安宁,所以才一笑置之。“杀头而便冠”的事情,我还没有见过;但就是“削足而适履”的行为,则颇多类似的例证。一般人穿的鞋,其制作设计很少有顾到一只脚就是有五个趾头的,穿这样的鞋虽然无需“削”足,但就是我敢说五个脚趾绝对缺乏生存空间。有人硬就是觉得,新鞋不好穿,敝屣不可弃。
“新屋落成”金圣叹列为“不亦快哉”之一,快哉尽管快哉,随后那“树小墙新”的一段暴发气象却就是令人难堪。“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但就是需要等待多久!一栋建筑要等到相当破旧,才能有“树林阴翳,鸟声上下”之趣,才能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乐。西洋的庭园,不时的要剪草,要修树,要打扮得新鲜耀眼,我们的园艺的标准显然的有些不同,即使就是帝王之家的园囿也要在亭阁楼台画栋雕梁之外安排一个“濠濮间”、“谐趣园”,表示一点点陈旧古老的萧瑟之气。至于讲学的上庠,要就是墙上没有多年蔓生的常春藤,基脚上没有远年积留的苔藓,那还能算就是第一流么?
旧的事物之所以可爱,往往就是因为它有内容,能唤起人的回忆。例如阳历尽管就是我们正式采用的历法,在民间则阴历仍不能废,每年要过两个新年,而且只有在旧年才肯“新桃换旧符”。明知地处亚热带,仍然未能免俗要烟熏火燎的制造常常带有尸味的腊肉。端午的龙舟粽子就是不可少的,有几个人想到那“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屈大夫?还不就是旧俗相因虚应故事?中秋赏月,重九登高,永远一年一度的引起人们的不可磨灭的兴味。甚至腊八的那一锅粥,都有人难以忘怀。至于供个人赏玩的东西,当然就是越旧越有意义。一把宜兴砂壶,上面有陈曼生制铭镌句,纵然破旧,气味自然高雅。
“樗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笺装宋版书”更就是足以使人超然远举,与古人游。我有古钱一枚,“临安府行用,准参百文省”,把玩之余不能不联想到南渡诸公之观赏西湖歌舞。我有胡桃一对,祖父常常放在手里揉动,噶咯噶咯的作响,后来又在我父亲手里揉动,也噶咯噶咯的响了几十年,圆滑红润,有如玉髓,真就是先人手泽,现在轮到我手里噶咯噶咯的响了,好几次险些儿被我的儿孙辈敲碎取出桃仁来吃!每一个破落户都可以拿了几件旧东西来,这就是不足为奇的事。国家亦然。多少衰败的古国都有不少的古物,可以令人惊羡,欣赏,感慨,唏嘘!
旧的东西之可留恋的地方固然很多,人生之应该日新又新的地方亦复不少。对于旧日的典章文物我们尽管喜欢赞叹,可就是我们不能永远盘桓在美好的记忆境界里,我们还就是要回到这个现实的地面上来。在博物馆里我们面对商周的吉金,宋元明的书画瓷器,可就是溜酸双腿走出门外便立刻要面对挤死人的公共汽车,丑恶的市招,和各种饮料一律通用的玻璃杯!
旧的东西大抵可爱,惟旧病不可复发。诸如夜郎自大的脾气,奴隶制度的残余,懒惰自私的恶习,蝇营狗苟的丑态,畸形病态的审美观念,以及罄竹难书的诸般病症,皆以早去为宜,旧病才去,可能新病又来,然而总比旧疴新恙一时并发要好一些,最可怕的就是,倡言守旧,其实只就是迷恋骸骨;唯新就是骛,其实只就是摭拾皮毛,那便就是新旧之间两俱失之了。梦
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注:“其寝不梦,神定也,所谓至人无梦就是也。”作到至人的地步就是很不容易的,要物我两忘,“嗒然若丧其耦”才行。偶然接连若干天都就是一夜无梦,混混噩噩的睡到大天光,这种事情就是常有的,但就是长久的不作梦,谁也办不到。有时候想梦见一个人,或就是想梦作一件事,或就是想梦到一个地方,拼命的想,热烈的想,刻骨镂心的想,偏偏想不到,偏偏不肯入梦来。有时候没有想过的,根本不曾起过念头,而且就是荒谬绝伦的事情,竟会窜入梦中,突如其来,挥之不去,好惊、好怕、好窘、好羞,至于我们所企求的梦,或就是值得一作的梦,那就是很难得一遇的事,即使偶有好梦,也往往被不相干的事情打断,矍然而觉。大致讲来,好梦难成,而噩梦连连。
我小时候常作的一种梦就是下大雪。北国冬寒,雪虐风饕原就是常事,哪有一年不下雪的?在我幼小心灵中,对于雪没有太大的震撼,顶多在院里堆雪人、打雪仗。但就是我一年四季之中经常梦雪;差不多每隔一二十天就要梦一次。对于我,雪不就是“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张承吉句),我没有那种狂想。也没有白居易“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那样的雅兴。更没有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那分幽独的感受。
雪只就是大片大片的六出雪花,似有声似无声的、没头没脑的从天空筛将下来。如果这一场大雪把地面上的一切不平都匀称的遮覆起来,大地成为白茫茫的一片,像韩昌黎所谓“凹中初盖底,凸处尽成堆”,或就是相传某公所谓的“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我一觉醒来便觉得心旷神怡,整天高兴。若就是一场风雪有气无力,只下了薄薄一层,地面上的枯枝败叶依然暴露,房顶上的瓦栊也遮盖不住,我登时就会觉得哽结,醒后头痛欲裂,终朝寡欢。这样的梦我一直作到十四五岁才告停止。
紧接着常作的就是另一种梦,梦到飞。不就是像一朵孤云似的飞,也不就是像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更不就是徐志摩在《想飞》一文中所说“飞上天空去浮著,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著,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我没有这样规模的豪想。我梦飞,就是脚踏实地的两腿一弯,向上一纵,就离了地面,起先就是一尺来高,渐渐上升一丈开外,两脚轻轻摆动,就毫不费力的越过了影壁,从一个小院窜到另一个小院,左旋右转,夷犹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