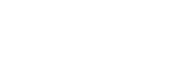《二大爷散文最新7篇》
以下是可爱的小编为大家分享的二大爷散文最新7篇,欢迎参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看车的大爷散文 篇1
看车的大爷散文
又是满当当了。我不由地低声嘟囔。电动车明早又不容易推出了。谁让我们这个小区的停车场,不,应当是停车间太小了。
对了,刚才进门时看车的大爷不是坐在门口吗?跟他说一声。停好车子,我一边往外走一边在心里暗自想着。
大门口并没有灯光,大爷就在阴影里凉椅上躺着。师傅,明早别把我的车往里推,我一大早要用车的。我对着那个模糊的人影小心地说着。
黑暗中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应。就如同一块石头被吸入深潭里,连泡都没有冒一个。我有些懊恼,往阴影里又挪了两步,仔细地瞅了瞅,确实是看车的老大爷廊形啊。
难道是我没有喊“师傅”,我分明记得喊过了;难道是我说话的语气太张狂?我分明把声音降低到最低度,语气调整到最温柔。还有什么不满意?我跺跺脚,当然是轻轻地。
哼,这么冷的天气还躺凉椅,冻感冒你。我狠狠地想道。一扭身朝回家方向走去。
明早他会帮我把车子赶出来吗?电动车被前后左右的摩托车围困着,根本就无法突出重围,即使偶尔有个空隙,拐弯也需要把车子往旁边拖一拖,才能拐过弯。可是,我的电动车那么重,费我的。九牛二虎之力难以提动。想到明早一定要按时上课,我就担忧电动车的进出。所以,走时才这么央求看车的大爷。
说是央求,一点也不过分。自从把电动车停在这个停车间,骑进骑出的,从没有听到看车大爷的笑声,更别说看到他的笑脸了。他的脸总是一片愁云惨淡,这片愁云好像随时都会滴落出水珠下来。
第一次赶不出车子的时候,我左挪右移,车子仍然纹丝不动,眼看快要迟到了。我跑到门口,求助于看车的大爷。
他等我说完,缓缓地站起身,慢腾腾地朝里面走去。我急冲冲地走在前面:“师傅,麻烦你快点,我快要迟到了。”大爷没有作声,脚步也丝毫没有更快。
看车的大爷虽然走路慢,力气却很大。他三下两下就把我的电动车从包围圈里挪移出来。可是,那天,我上班还是迟到了。
把电动车骑出来真是个烦恼的事儿。我每天骑进骑出时,都会把自认为最亲切的微笑带给大爷,想跟大爷套套近乎,让他帮我移动车子。
可是,他从来没有跟我搭过话,包括,每次我跟他道谢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抬过眼,回答我一声:不用谢。
看车的大爷虽然没有一次应承过我,但是,他只要看到我进到车棚里有一会儿没出来,也会慢腾腾地走进来,帮我把车子搬动出来。我也曾怀疑看车的大爷是哑巴或者是聋的,可偶尔,也会看到他跟其他的人打过招呼说过话。
今天也同样如此。我主动跟看车的大爷说话,纯粹不是自讨没趣吗?
唉,我在心里长叹了口气:有人默默地做了不一定会说,有人会说了但不一定会认真去做。也许,人,每人,都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不理解也不被别人所理解。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生活着,都会有他存在的理由。不要强求他和你和我是一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他曾经历过什么或正在经历着什么。我安慰着自己,给自己上了一碗心灵鸡汤。
第二天,我早早醒来,为的是避免今天再次迟到。还没有到停车间,远远地就看见我的红色的电动车映入我的眼帘。
哈哈,不用跑到停车间里面排除万难推出车子了。我喜出望外,大爷站在门口,眼神空洞,似乎在看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把钥匙插入锁孔里,轻轻地旋转着车把,电动车缓缓向前移动。“大爷,谢谢你!”走过大爷身边,我大声对他喊道。
大爷依旧没有发声。但我却清晰地看到他的眉峰往上挑了挑,他是在笑吧,他一定是在笑。
一股甜甜的暖意涌入我的心头。
一天的工作应当都是这样的心情吧。
描写人的经典故事:二大爷 篇2
二大爷煎的一手好饼子。
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是二大爷的煎饼摊儿。人们调侃二大爷 :二大爷,您把摊儿支这儿,想赚学生娃们的钱?二大爷头也不抬,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赚你个脑壳,就知道赚钱。
二大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负过伤。享受政府津贴。二大爷一直没有成家,所以无子无女。但是,二大爷却偏偏喜欢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儿,二大爷都喜欢。论二大爷的条件,完全可以不弄这个煎饼摊儿,过清闲的日子。
二大爷的煎饼地道,味美可口,香飘四溢。闻着味儿就能找到学校。学校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这里的条件相对落后一些。学校也没有住宿的条件,孩子们都是走读生。学生娃有镇上的,有周边不远的村里的。二大爷就是为了这些娃们支的煎饼摊儿。
一个味美可口的煎饼,只卖收娃们五毛钱。这根本就不够煎饼用的成本。二大爷说,过得去就行了!不能多收,孩子们没钱。我又不是卖煎饼……所以,很多时候,二大爷是贴钱卖煎饼呢。二大爷还说,只要能看见学生娃们,就开心。
久而久之,学校、煎饼、二大爷、学生娃便连在了一起。
每天,二大爷天不亮,就早早起来了。收拾好一天用的东西,就出发了!要赶在学生娃们来校前,这样就不耽误孩子们吃煎饼了。
”二大爷,来个煎饼!“
“二大爷,俺要加两个蛋的煎饼!”
”二大爷,二大爷”……叫声不断,二大爷忙的不亦乐乎……
一天,学生娃们发现二大爷没有来。一天两天,好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二大爷的影子。娃们急了,到处打听,才知道二大爷住院了,说是肺癌晚期,就在镇上的医院里。
“吱呀”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二大爷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液体缓慢地流进二大爷枯瘦的身体里。二大爷听到动静,,慢慢地睁开眼睛,看见校长和孩子们,他腊黄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有几个孩子哭了起来。二大爷有气无力地说 :“校长,孩子们别哭,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
他接着又说 :“好孩子们,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啊!可能以后二大爷再也不能给你们煎饼子吃了!“他边说边用一只手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薄薄的纸包,交给了校长。二大爷说 :“我一辈子无儿无女,但是非常喜欢孩子们,看着他们就是看到了希望。这里面有一张卡,上面是我一辈子的积蓄,五万块钱,我这病也治不好了!不能再糟蹋钱了,这点钱给孩子们买几台电脑吧,孩子们用的上……“
二大爷走了!出殡的那天,所有的孩子们都哭成了泪人……
人们说,别看二大爷无儿无女,走的风光,孝子又多……
二大爷真的走了,学校门口再没有煎饼的味道了……
作者|郭利
公众号:小说大世界
大爷的远征军岁月的散文 篇3
大爷的远征军岁月的散文
清明是花最哀伤的日子,漫天怒放的是离愁伤感;清明是雨最幽怨的日子,纷纷细雨中满是欲断魂的行人;清明是心最虔诚的日子,静静倾诉着怀念和牵挂的愁绪。清明让我想起了我的大爷,想起了他的远征军岁月。9年前,92岁的大爷在那秋雨飘零的深秋走完了他跌宕坎坷的一生。
那是1942年,贫困交加的大爷自卖壮丁,想到军队去混口饭吃,以免饿死。谁知他运气不好,一到部队就被马不停蹄地运到昆明,然后连夜坐汽车到了中缅边界。这时他才知道他所在的第5军,是到缅甸打的远征军,保卫当时的生命线——缅滇公路。大爷随着部队一到缅甸就上了战场,没有一点战斗经验的大爷被战场上那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情景惊呆了。但大爷聪明,没多久枪法就练得又好又准,他个子矮小很机灵,后来当了侦察员。一次到前沿阵地去侦察,被敌人发现了,他爬上树躲过了敌人,并在树上把敌人阵地看得清清楚楚,带回了有用的情报。
后因多种原因战斗失利,第5军杜聿明将军奉命撤退,并作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取道缅北密支那野人山回国。那是一片绵延千里,至今都还是的原始森林,部队很快就在茫茫大森林中迷路了。不久,他们吃光了带来的粮食,杀完了战马,部队陷入饥饿之中。前路艰险,林中猛兽成群,蚂蝗遍地,很多人因饥饿、疾病死去了。还有一些人不堪折磨,绝望中相互射杀,场面惨不忍睹。大爷矮小利索,很会爬树,常常在树上找些野果充饥。有一天他和三个战友一起去找食物,回头再也找不到集体了。雨下个不停,突然而来的`山洪卷走了一个战友。他们还沉浸在悲痛中,一条毒蛇又咬伤了一个战友,另一个战友给他吸毒,不幸两人都中毒身亡。眼睁睁看着战友在自己身边倒下,大爷痛苦不堪,剩下他孑然一人,陷入了绝境。他小心翼翼的躲着原始森林里的食人蚁、蚂蝗,身边尸骨遍野,恐怖异常,险象环生。漫无目标的转啊转啊,他的裤脚被什么绊住了,低头一看,死人堆里伸出一只手来拉着他,他着实吓了一跳。翻开死人他拉出了一个战士,这人饿的没有了一点力气,大爷赶紧把采的野果给他吃了。他们两个结伴而行,一路上饿殍遍地,尸骨累累,惨绝人寰。他们看到一棵大树下靠着一个战士,睁圆的双眼直视前方,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个烟袋。掰开他的手,看见那个大红的烟袋上绣着一对戏水的鸳鸯,这一定是他的妻子送给他的。可以想象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多么的想念亲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大爷只好把烟袋放回他手里,把他的眼睛合上,告诉他安息吧,人们会永远记住他的。后来结伴的战友也因为寒热高烧病死了,再一次只剩下他一个人。正在他转得天昏地暗的时候,突然波涛汹涌的怒江出现在他面前。起初大爷以为看花了眼,以为是幻觉是海市蜃楼,揉揉眼看清了是一条江。后来他经常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望着大江一筹莫展的时候,江边漂来了一根很大的烂木头,又累又饿的他抓住木头爬上去后就失去了知觉,任凭江水把他漂到哪里。他醒来已经在对岸了,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但再也找不到他的部队了,他只好一路讨饭,几经生死回来了。
大爷从不讲他的远征军岁月,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年,才断断续续地跟我讲了一些他和远征军的故事。他常常感叹能从野人山回来,他是多么幸运的啊!是啊,清明来了,不知和战友团聚了的大爷,是否安好?
龟大爷 篇4
龟大爷一天时间,有十分之一是吃肉,有十分之二是看风景,有十分之七的时候,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是和周公去下棋,或缩在壳里不知做什么。
我们的龟大爷也是很难服侍的,有一次,我拿了以块很好吃很好吃的熟肉给它,刚扔下去不够一秒钟,龟大爷缩进了壳里,不吃?不可能吧。过了一会儿,它把头伸出来,用憎恨的眼神看着我,我赶紧把熟肉拿起来扔了,我又拿了一块生肉放进去,它才狼吞虎咽起来,妈呀,冷血动物。
我爱我的乌柜,虽然它有点烦,又挑剔,但我还是喜欢它。
二大爷散文 篇5
二大爷散文
在小时候生活过的D村,与我们家走得最近的,就是二大爷了。他姓余,在家族中排行第二,晚辈们见到他都称呼他“二大爷”。
我们家和二大爷家都住在D村的西边,他家位于西边的南部,我家位于西边的北部,隔着中间被自发踩出小路的两块玉米地遥遥相望。
记得每年腊月初始,都能看见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子从南到北穿越玉米地,拎着一个布袋子,朝我家的方位走来。有时候在外面疯玩看见他来,猜个八九不离十是到我家,还故意问他:“二大爷,上哪啊?”
“上你们家。”二大爷的回答毫无悬念。
“二大爷,袋子里装得什么呀?”我也是明知故问。我知道那里装的是粘豆包。
二大爷家每年淘米做年豆包都很早,进入腊月就开始做,而我们家总是滞后,这样就出现了时间差。二大爷总是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在我们翘首企盼吃粘豆包的时候,及时给我们送来。
这个时节,看见了二大爷,就相当于拿到了粘豆包。因此,我们姐妹几个随着二大爷往家走。二大爷骨瘦如柴,身材矮小,戴一顶破旧的狗皮帽;他眼窝微凹,颧骨稍高,牙齿也“退休”了大半,在东北乡村凛冽寒风的吹拂下,眼睛里不时地溢出泪水。看着这样一个被岁月和生计将要耗尽变得苍老的老头,我心里生发出丝丝感动。
到了家里,二大爷和父母寒暄几句,我们用余光不停地扫视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布袋,心理有一个愿望不用商量就能达成共识:二大爷说完话了就离开吧,我们分吃粘豆包!在人家没走的时候不能打开袋子狼吞虎咽,这样的家教底线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克制做到的。
熬到二大爷离开,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布袋取出粘豆包自动自觉地吃了起来。
二大爷家的粘豆包,就是比我自家的好。我们家的粘豆包,兑进黄米面的玉米面比例偏大,黄米的粘度降低,用专业的说法就是有点“笨”。豆馅里放糖精的量也把握不好,不是稍苦,就是不甜。二大爷家的粘豆包,黄米面、玉米面的比例掌握的恰到好处,吃着口感滑腻;用豆角豆做馅,并不捣成泥,半碎不碎,面乎乎的,甜丝丝的。二大爷家的粘豆包,皮薄,馅大,在食品匮乏的童年,就相当于冰淇淋,汉堡包,比萨……即便二大爷送来的时候,已经被严冬的气温冷却变硬了,那种“哏赳赳”的口感,也让我们心满意足。
我父亲从小失去母亲,脾气暴躁古怪,我们家是后“移民”D村的,和村邻们相交不深,二大爷是父亲少有的几个朋友之一。据说,有一年冬天,二大爷去与D村毗邻的E村亲属家参加婚礼,碰巧心情不顺,喝得酩酊大醉。平时不善言谈的他,夸夸其谈,从祖上说起,追述了家族的发展历程,个人的奋斗经历。人在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往往会将自己的一生,从头算起。二大爷不仅自评了自己的一生,还评价了祖上四代,向在场的人道出压抑已久的心曲。
喝酒误事误时。二大爷是傍晚被亲属送走的最后一批客人。亲属们或许以为外面的寒风很快会拂去二大爷神经中的醉意,帮他顺着来路回到家里。可是趔趔趄趄走到D村边冰冻的河上,他就误以为是家里烧得热乎乎的炕头,倒下睡着了。
凑巧我父亲下班骑自行车回家,路过河面被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绊倒,刚要开骂,看出是一个人,仔细辨认,是二大爷。父亲本性中善的一面凸现而出,催促他把二大爷送回家,两人也结下了虽未结拜胜似兄弟的深厚情谊。二大爷长父亲20多岁,算是忘年交吧。
我家孩子多,靠父亲的微薄工资度日,条件很一般。不过,由于是非农业户,可以去粮店领粮,领到白面。逢年过节的,偶尔我家也送给二大爷家一袋面,礼尚往来的道理,父亲还是明白的。
在我印象中,二大爷给我家送东西的`次数远远多于我家回赠于他的。
读小学的时候,午休一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去掉路上约50分钟的时间,吃饭时间不足10分钟,大人总是很忙,也不可能专门为中午回家的孩子准备正餐,多半是吃一口剩饭便急匆匆往回返。清明节那天中午,桌子上就有可能摆着6本书那么厚的黄面饼,让我们心花怒放,莫名地惊喜。饼的两面色泽金黄,似乎炫耀制作它的主人技术多么娴熟,火候把握的又是那么精确;那饼向我们的鼻子释放出微酸的、调动食欲的香气,也在表明黄面至少通过了一夜的发酵;饼的薄弱处,星星点点露出豆馅的深紫色。在微凉的初春时节,吃上出锅不久热气腾腾又香又甜又粘的黄面饼,一刹那甚至让我们体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待遇。
东北乡村有清明节淘米烙黄面饼子的习俗,而我家很少受习俗的约束。不用问也能断定这些黄面饼从二大爷家锅里盛出直接送来。返回学校的路上,我拿着一块饼小口小口地吃,吸引同伴们羡慕的目光,诱惑他们不停地吞咽涎水,从中得到一点心理上的优越感。
二大爷家最拿手的食物不局限于粘豆包和黄面饼,还擅长做玉米面发糕。
喇叭裤风靡一时的年代,这里要修建省城达我们镇上(据财商高的村民估算相当于5元钱5元钱铺起来的)的柏油路,从各地征集的民夫分散居住在地方宽敞的农家。一般不会安排在我们非农业户家里。
住在二大爷家的幸运筑路者有时候午饭的主食是玉米面发糕。那个年代,玉米面饼是最普及的被很多人吃烦了的食物,我家也是。尤其是用从粮店领回来的陈玉米面贴出的饼子,粗糙,干硬,咽到嗓子眼往往就会受到重重阻挠,再依靠本人坚强的意志力强制送到食道里。而二大爷家用新鲜的玉米面蒸出的发糕效果就大相径庭,松软酸甜,香气飘散。二大爷似乎猜透了我们小孩子的心思,每每蒸发糕,都要给我们送一大盆,我拿起相当于四块豆腐大的发糕,一会儿工夫就能消灭掉,后来比之于奶油生日蛋糕,后者相形逊色。那种酸甜度的精准调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我怀猛儿再次想吃的时候,深受欲吃不得的折磨。
二大爷用他补人之无的智慧与善良,回报了一位帮助过他的朋友,让他的孩子们从中受益,在贫瘠的童年品尝了自家不能做到完美的家乡特色美食,津甜了童年的某些时刻,并延续到很久的将来,在夜深人静的电脑桌前,用键盘追述那种不可复制的体验。也反思由于自己的不慎造成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爱屋及乌。二大爷和父亲的友谊,理应顺理成章地被两家的子女承袭。
可由于我的淘气顽皮,却伤害了他的儿子。
他的小儿子小海比我大5岁,脖子下面包着锁骨的皮肤弹性不足,松弛下垂。别人开玩笑时说他“哈拉皮子带板筋”。我看到同龄人和他开此种玩笑他并未发火,又不甚理解其中含义,也学着别人的说法对他喊:“哈拉皮子带板筋!哈拉皮子带板筋!”
他怒目圆睁向我跑来,摆出要打人的架势,我撒腿就跑。才知道这句话一定不是好话,闯祸了。一个女孩子闯祸到被人追打,是多么羞耻的一件事情啊。
有一次放学路上,我和新搬到D村的同学结伴往回走,“不幸”迎面遭遇小海,他面露怒色跺脚伸拳做出攻击我的姿势,我还是使出三十六计中的上策――走,其实是跑。他并不穷追,也许只是想吓唬吓唬我罢了。
同学对我表示出无限的同情,叹了一口气,说:“冤家路窄,咋碰上他了呢!”
我心里却想,一来我家和他家不是冤家,是D村相处最融洽的两家;二来怎么能怪他呢,是我惹祸在先。
后来明白了“哈拉皮子带板筋”的含义。“哈拉皮子”,指(牲畜)肉间的软组织,具有蒸不熟煮不烂的缺点,“哈拉皮子带板筋”形容不好对付死缠活赖的人。后来我们教师间交流,私下也把不好管教的学生称为“滚刀肉”,我以为相当于“哈拉皮子带板筋”。明显的贬义词。谁愿意这样的贬义词用在自己的身上呢?
而我,因缺乏慎重的素质,多余轻率的秉赋,祸从口出,伤害了二大爷的儿子。虽不是什么滔天大祸,势必会给小海留下“不懂事儿”的印象。本来应该精心照顾父辈栽下的友谊之树,施肥,浇水,而不是去折枝掐叶。
家庭之间的交情,需要用真诚的心态及正确的方法去经营,否则,就可能面临中途夭折的结果。
我和二大爷的后代没有什么联系了,不能不说这是遗憾的结局。
还念我的二大爷散文 篇6
还念我的二大爷散文
我二大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脾气有点倔,直心眼儿,热心肠。年轻时娶过两个老伴,都没生育。后来一直单身。到了古稀之年,才和我最后这个二娘结合在一起。可两位老人没过几年,我这个二娘也去世了。(按农村迷信说,我二大爷有点克老婆。)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和我二大爷过多接触的。
那天我刚下班,我爱人急忙回来对我说:“后院二娘有病了,你快去看看吧!”我急忙跑到后院。我一进屋,屋里有好几个老太太,其中有一个老韩太太,说是我二娘起了‘‘臭翻”,已经挑完了,一会就好了。过了一会,我看病情不见好转,于是我对我二大爷说:“上医院吧?”我二大爷同意。我急忙上生产队找队长,队长给个马爬犁,我用这个马爬犁——唯一的交通工具,和周玉森(我二娘的远方侄子)拉着我二娘去江口医院。江口离我们屯有十几里路,到那天已经黑了。值班大夫捂着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也没捂着过来,说是心脏病。(当时的各方面条件太差)我只好连夜步行赶回村里,给我二大爷报信。又急忙和我二大爷返回医院。
农村有句俗话,侄子门前站,不算绝户汉。我二娘的一切后事的规矩,自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后事完毕,我二大爷非常苦闷。我们屯有一个老郭头,好说合事。当天晚上,就跟我二大爷说:“我看这么行不?让两个小孩上你这来吧,侄子也就是儿子。你要同意我去跟两个小孩说。”我二大爷同意。老郭头和我们一说,我们乐够呛。我们当时是最困难的时候,能上我二大爷家,赶上上天了。于是,第二天我们就搬到我二大爷家。
我二大爷家是标准的农户家庭,我们来后,要讲农村过日子家把式(工具),要啥有啥。当时已进腊月了,过年的东西都不用买了,米、面、还有猪肉,猪头、猪下水,好丰盛啊!当天晚上,我和爱人半宿没睡觉,开始收拾屋,归拢东西。原先是无产阶级,现在是小地主了,虽说没钱,可过日子的东西有哇。你说能不高兴吗!就在我们整理我二娘的衣服时,发现兜里有二十元钱。当时二十元钱,是很耀眼的数字。我爱人拿在手里,热乎热乎,瞅瞅我,我瞅瞅她,然后我们把它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我们知道,这二十元钱,我二大爷肯定不知道,但我们的道德品质在阻拦我们,虽然穷,但这钱不能要。第二天早上吃饭,我们把这二十元钱告诉了我二大爷。我二大爷把钱掏出来揣在兜里没有吱声。
那时农村生活苦,我二大爷家还算不错,有点细粮。我爱人经常给他做点小锅。蒸点大米饭了,下点面条了,蒸碗鸡蛋糕。当时他在大队给看屋, 回来吃完饭就走,不在家呆,也不吱声。那天晚上,他吃完饭说:“明天早上,我不回来吃了,”我爱人问“那你上哪吃去”?“不回来就是不回来,问那么多干什么!”我二大爷脾气倔,我们不敢问了。
第二天早上,我爱人做的是大馇子水饭 ,咸菜条。我们刚要吃,我二大爷回来了。一看,我们吃的是大馇子和咸菜条,脸上露出一种说不出地表情,说:“我昨晚剩的大米饭,咋没热上?”我爱人说:“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吗?”我二大爷说:“我说是让你们吃,老给我留着干啥?”我二大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们明白了,这是在考验我们。
这种情况以后又发生过几次,每一次,我二大爷的脸上都露出相同的笑容。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二大爷也一天比一天乐呵了。话也比以前多了,有时晚上吃完饭,还和我们唠一会嗑。不知不觉,春节就来到了。我二大爷特别高兴,又往家买糖,又买冻梨,来回走还哼着小曲。这个年过的很丰盛,有大米白面,猪肉粉条。三十晚上他和我们一起包的饺子,一起吃的年夜饭。吃饭时,老人家拿出二十元钱,给我们一人十元,说是压岁钱。多大了,还压岁钱?实质是对我们俩地奖励。
过了年,我二娘的一个远房侄子和他儿子,来悼念我二娘。我二大爷下令,
让我们好好招待。我们不敢怠慢,又把过年没吃完的东西拿出来,我二大爷又买的酒 。俩人呆了三天。临走时,我二大爷说:“你们大老远来,我很感动。你姑姑 也没留下啥好东西,这个戒指算是最值钱的'了,你们拿去吧,做个纪念。另外,她还有几件衣服,你们相中那件就拿那件。”说完把戒子给了他们。这爷俩非常感动。我们也非常支持这种做法。
转眼到了开春,天气暖和了。到有活的时候了,这可是我二大爷的强项。他的一生就是乐意干活。每天刚一亮,三、四点钟,他就回来了。然后敲着窗户喊:“啥时候了,太阳照腚了,起来!起来!”我俩急忙起来。你要是贪睡,不起来,他可不高兴了,开口就骂:“他妈巴子的,快起来!年轻人捂被窝子,能过好日子吗?!”然后,嘴里骂着,把外屋的木板井摇得哗哗直响。你想睡觉?没门。我俩一开始,很不高兴,年轻人,早晨起来那滋味成是难受,可是不起来不行啊!可一细想,人家七十来岁,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们好。思想一想开,自己就有了动力,我不用他招呼了。不等他回来, 我已经在小园里干上了。他回来时,我已经铲半截垄了。啥活没等他干,我就干完了。老爷子一看,高兴。
二大爷的勤劳,逐渐“传染”给我,我也是天一亮,就躺不住了。急忙起来干点啥。后来发展庭院经济,全靠早晚的时间。白天上班,没时间。我二大爷的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到现在,我还继承着,始终没扔。
我二大爷是我以后发展经济的很好帮手。我在创业上所取得一些成绩,有我二大爷的很大功劳。我扣大棚,卖韭菜,卖黄瓜,养洋鸡,种水稻,每一样都渗透着我二大爷的汗水。星期天我和我爱人去城里卖菜,卖鸡蛋。回来时,老人家一手领一个孩子,在门口望着我们,锅里已经给我们烧好了粥。家里的洋鸡,他给喂,小园里的草他给薅………。
我非常感谢我二大爷! 没有他老人家,我当时就会走投无路;没有他老人家,我不会这么快脱贫致富;没有他老人家,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已经眼泪哗哗地流,无法止住。
到了晚年,他老人家的腰已经弯了,可是他还是那样地勤劳,还是那样的简朴。那样的护着这个家。他有病躺在后屋炕上时,还用一只手在哄园子里的小鸡……。
八三年,我二大爷八十六岁,患了脑血栓,当时的医疗条件也不好,在医院住了几天大夫说:‘‘回去吧,这么大岁数治不好了。”回来后,不到一个月,老人家就走了。临走时,攥着我和我爱人的手说;‘‘你……就是我的……亲儿子,淑华……就是我的……亲闺女。”
二大爷,安息吧!孩儿永远怀念您!
老陶大爷的散文 篇7
老陶大爷,山东人,总爱把“六”说成“柳”,而且声音拖得老长。据说,他自小逃荒要饭来到安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后来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成了我们曹家庄唯一的一户姓“陶”的。
记忆中,老陶大爷一直为生产队喂牲口,这活儿又脏又累,还要起早贪黑。当初,队长曾经物色了好几个人,但是他们都不肯干,唯独老陶大爷愿意,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因此,老陶大爷对侍弄牲口有了经验。据说,无论牛马驴骡,如果生了病,老陶大爷只要摸摸它的鼻子,看看它的舌苔,拍拍它的肚子,立刻便能十拿九稳地找出病在哪里;然后采用偏方,煎药灌汤,手到病除。
我七八岁时,最爱和伙伴们一起到牛屋里玩耍。老陶大爷看见我们总是很高兴,他经常在通红的柴灰里为我们烧几个大红芋,有时候也拿出作牛料用的黄豆招待我们,那豆是炒熟了的,嚼起来格外香。看到我们吃得满嘴乌黑,老陶大爷就呵呵地笑着:“小兔崽子,肚子饱了还不回家?”
寒冷的冬天,我们常在晚饭后去牛屋里烤火。老陶大爷先把牛牵到撒了一层麦糠的干燥地方,接着又抡起膀子,用一只大木锨将一堆堆牛粪铲到屋外去,然后再给槽上的驴和马拌好草料。等这一切忙完后,他才吹熄挂在墙上的手提灯,慢条斯理地点燃一堆柴。顿时,牛屋里烟雾弥漫,四壁温暖。我们围着火堆听老陶大爷讲故事,尽管被烟熏得涕泪横流,但久久不忍离去。有一次,我竟躺在热烘烘的草堆里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却不知啥时候钻进了自家的被窝里,父亲告诉我是老陶大爷把我背回来的。
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了,农村人开始种自己的地,喂自己的牛。那几年,牲口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犁耕耙拉全靠它。因此,时常有人登门向老陶大爷请教,他从来不推辞,不管多忙多累,只要开口,便有求必应。那年,庄东头的强叔家的骒马赶上下驹子,把他请了去,老陶大爷整整一夜没合眼,眼睛都熬肿了,强叔很过意不去,就打了两斤散酒表示谢意,老陶大爷说啥也不收,反而送给他几斤芒大麦,说“骒马要加料,吃这个有好处。”
日子渐渐好起来,年近七十的老陶大爷须发斑白了,而身子骨依然硬朗得很。种庄稼实行了机械化,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喂牲口了,老陶大爷总觉得心底空落落的。正巧,这年刚开春,从外地来了个马戏团,领头的听说老陶大爷饲养牲口有一套,就软缠硬磨地求他去喂马。老陶大爷对牲口有感情,想想两个儿子都已成了家,又没啥心事,便爽快地答应了。
腊月天,跟随马戏团走南闯北的老陶大爷回来了。他身上披着霜花子,面容憔悴,步履蹒跚。三天后,居然卧床不起,不吃也不喝,只对家人说:“胸口疼,闷得慌。”到医院检查,医生讲病人内脏受了伤,由于未能及时诊治,病情已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了。原来,在一次演出中,有匹马被绳子牢牢地绊住了腿,老陶大爷弯腰解绳子,那马大概受了伤怕疼,竟抬起腿朝他的前胸就是一蹄子。当时,老陶大爷躺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直到咽气前,老陶大爷才说出自己的病因。儿子哭喊着追问他:“马戏团在哪?领头的名字叫什么?”可是老陶大爷只微弱地摇摇头,断断续续地重复那句话,“人家出门……在外……也不容易……”
就在那年腊月二十八,全村人含泪将老陶大爷送下地。我亲眼看见许多人,在他的坟前烧着用纸扎成的牛和马。
【孟婶】
最初见到孟婶,是在她与秃叔的婚礼上。当时,孟婶只有十八岁,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身材高挑,但并不显得单薄。孟婶不爱笑,笑时,腮边的酒窝儿格外深。全村人都说孟婶漂亮,人好,只是嫁给秃叔有点儿亏。
孟婶嫁给秃叔的同一天,秃叔的妹妹嫁给了孟婶的哥哥,这在当地叫做“两换亲”。起先,正读高中的孟婶宁死不从,但最终没拗过父母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秃叔人老实,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头顶秃,个儿矮,干活没力气,人送外号“秃老蔫”。孟婶比秃叔年轻十几岁,俩人站一块总让人感觉别别扭扭的不舒坦。婚后,没多久,秃叔家就变了样,虽说住的是几间破草屋,但经孟婶一拾掇,马上就变得整整齐齐、亮亮堂堂的。
孟婶特能干,丢下锄头摸苕帚,一天到晚闲不住。土地承包到户后,孟婶让本庄的男人们直咂嘴,铡草、喂牛、耕地、扬场……说出来怕有人不相信,那年六月里,孟婶顶着毒日头,腆着怀了孕的大肚子,一天下来居然割倒二亩麦。不干咋行呢,秃叔身小力薄,笨手笨脑,正儿八经的农活确实没指望。
有一年正收麦,半夜里天阴了,孟婶将鼾声正浓的秃叔揍起来,拽着他到场上把散开的`麦子垛成垛儿。一开始,秃叔用杈子将麦个子挑上垛,孟婶爬上垛,一层一层地摆,当垛到一人多高时,秃叔就呼哧呼哧喘粗气,无论怎么使劲,那麦个子就是挑不到垛上去。没办法,孟婶索性与他换个位。谁知过了一阵子,秃叔竟躺在高高的麦垛上睡着了,喊也喊不醒。孟婶气得瘫在地上,抚着肿痛的手腕子,一边哭一边骂。
生活眼瞅着富裕起来了,秃叔家的草屋换成了三间砖瓦房,添置了在那时还算稀罕的黑白电视机。然而,孟婶却不开心,依旧很少笑,依旧默不声响地干活儿。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孟婶为秃叔生了两个男孩子。生过孩子的孟婶比以前更好看。于是,经常有人跟孟婶开玩笑,说她凭现在的年龄和容貌,准能找一个没结婚的小伙子。孟婶不恼怒,有时也跟人家斗两句嘴,然后就转过脸去发一阵子呆。而秃叔只在一旁抽闷烟,不吭声,脸色阴沉沉地,很难看。
后来不知咋地,有关孟婶的传言逐渐多起来,有的说她经常偷偷地去见一位高中时恋爱过的男同学,那同学至今未成家,还在痴痴地等孟婶。还有的说孟婶生的第二个男孩跟秃叔一点儿都不像。这一切被传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由不得你不信。
孟婶仍跟往常一样家里地里不停地忙。但是,秃叔心里憋得慌,问又不便问,只能暗地里细观察,瞎琢磨。本来,得到孟婶这样的老婆,他心里从来就没踏实过。
这一年,孟婶趁农闲进了一趟城,由于时间仓促,临走时没来得及给秃叔打招呼。孟婶买来一台落地扇,还为秃叔及孩子们每人扯上一身夏天穿的新衣裳。当她兴高采烈地到家时,一向怯懦的秃叔竟迎头冲她吼起来:“谁要买的落地扇?你是从哪挣来的钱?”孟婶一下子懵住了,当她终于弄明白秃叔心中窝火的原因后,没说啥,像根木头似地怔在那里老半天,眼里滚出几滴晶亮的泪。
天黑时,带孩子串门的秃叔回到家,用力推开堂屋门,却闻到一股刺鼻的农药味,扭头看去,惊见孟婶蜷缩在墙角里,胸前的单衣被抓破,口中还慢慢地往外冒着白沫儿……
孟婶死了,年仅二十六岁,葬在村外荒草凄凄的沟坡上。听说,这么多年来,人们时常在晚饭后看见秃叔领着两个孩子,跪在孟婶的坟前呜呜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