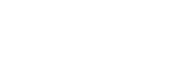《漂泊的散文》
漂泊的散文
多年以来,每每回想那些租房的岁月,心里就像深秋的水面,幽幽的飘浮着数点浮萍。
家,家是什么?从字形看,“家”就是一处房子,房子里住着相依相伴的亲人。不管是破旧小屋,还是奢华的豪宅,不是属于自己的房子,给人带来的,永远是萦绕心间,挥之不去的漂泊感。
1994年,我的父母迫于生活的压力,漂泊到株洲做服装加工生意。暑假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株洲,当看到他们租住的房子时吓了一跳。那是西郊的一层平房,周围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菜园。灰头土脸的三个平行房间,一间稍大的做厂房,里面放着几台缝纫机和一块裁板;另一间作宿舍,摆放着几张窄窄的竹床,一块黑色的大布将房间一分为二,男女宿舍各占一边;那间小房是爸爸妈妈的卧室,说它是卧室,只不过是放了一张床,剩下的空间都用来堆放布料、配料、服装的半成品和成品。坐在屋里,令人窒息的臭气,一阵阵地从外面灌输进来,紧闭门窗也无济于事,白天看苍蝇恣意飞舞,晚上听蚊虫持续轰鸣。尤其不方便的是,厕所距离住房有几十米,且有几十个人共用。这样的房租在当时是最便宜的。
一年以后,爸爸另外找了一处房子,虽然偏僻,但有上下两层,下面做厂房,上面住人。可上面一层是阁楼,冬天北风呼呼,夏天似蒸笼。那年暑假我们全家都长了痱子,脸上,脖子上,肚子上,背上,密密麻麻,出点汗便其痒无比,身上像爬满了无数条长嘴的毛毛虫。阁楼的地板滚烫,要等到凌晨以后才稍微变凉,下午时分在地板上洒点水,瞬间就会被蒸发。俗话说,搬一次家穷三年。因为各种不便,爸爸妈妈还是在西郊辗转了几个地方。几年后,才搬到了离市场较近的南郊。那是一栋较新的房子,空间比较宽敞,房子前面是个大院子,大门口两边种着几棵长青树。父母租下了整栋一楼,房东一家住楼上,每当有电话打来时,女房东的脸上乌云密布,靠在阳台上对着下面,极不耐烦的`喊:“楼下的,电话!”
快过年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房东的通知,不能继续租房给我们,理由是他儿子的女朋友怀孕了,得装修婚房。习俗中,正月不宜搬家,于是,在年关将近时,妈妈一个人在市场继续做生意,爸爸每天穿行在各个小巷,四处打听,寻找合适的房子。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大年三十的凌晨,当妈妈把我们叫醒来时,只见房间里堆放着,无数的大包小包,搬运工早已回家过年,我们姐弟互望着,直发愁。爸爸骑着三轮车,因为有好长一段上坡路,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后面推。在乌黑的夜里,寒风吹在脸上麻辣辣的。爸爸使劲蹬着三轮车,他喘着粗气,在凛冽的北风里,不停地擦拭额头上的汗珠。我们都没有说话,一趟又一趟,就像蜗牛一样,不知道跑了多少回,才把家搬完。
当把所有的物件搬到新家时,天渐渐亮了,妈妈带着我们分类整理,爸爸拿着工具安装厂房和铁床。当一个家再次诞生时已临近中午,妈妈突然想起,家里还没有准备过年的饭菜,爸爸骑着三轮车疾奔菜市场,到达时,平时堆积如山的菜市场,已空空如也,超市也已关门,幸运的是,最后买到了人家卖剩的半只羊,于是,在热闹祥和的春节里,我们全家五口,一天到晚,连续吃了几天的羊肉火锅,以至于后来好多年,家里都看不到羊肉。当我们渐渐长大,家里的生意越做越好,房子也越租越大,可始终没有达到买房的条件。漂泊在他乡繁华热闹的街头,那时在我的心里,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处完全属于自家的房子,就算房子再破烂不堪,只要和亲人相守在一起,过安稳的日子,就是幸福。
对于搬家,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但还是发生了戏剧性的一段。那年妹妹在外地读大学,由于搬家之前没有写信告诉她,当她兴冲冲地赶到家时,面对她的是人去楼空,查无此人,后来她打听了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我们的新家。当她突然出现时,妈妈不停地擦眼泪……
我们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但始终如无根的浮萍,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每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不知道下次何时要换到另一个地方。直到2002年,我们总算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有了真正意义的家,从此结束了忐忑的漂泊之旅。
2002年经过拍卖,爸爸买到了一栋二手房,三层楼,带个仓库,我们三姐弟也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对于那次搬家,一直记忆犹新,家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心里比过年还高兴。在后来的几年间,全家齐心协力,把服装加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三层楼房已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2005年,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爸爸买下了一块地,历时一年,一座4千平方的8层楼房拔地而起。我们三姐弟也各自成家,住在同一栋楼里。这座城,已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一直都能理解,那些为了拥有一本房产证,而甘愿将自己一生做筹码的“房奴”。也只有漂泊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居无定所的辛酸,也只有漂泊过的人,才明了安定是多么的重要。
漂泊很无奈,但在那些辛酸的日子里,沉淀出的厚重底蕴,和无法割舍的浓密亲情,都是一种横贯灵魂的财富,更让人珍惜当下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