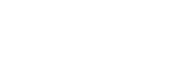《季羡林日记范文(通用4篇)》
《季羡林日记范文(通用4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季羡林日记】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季羡林日记 篇1
今天,我们学了第六课,是作家季羡林的《怀念母亲》。
这篇文章中写了季羡林六岁离开母亲,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母亲去世,他食不下咽,寝不安席,痛哭了好几天。从此,他失去了母亲,一想到母亲,他就会泪流不止,感到十分凄楚。他到德国之后,经常梦到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在1935年11月写的四篇感人的日记中,我读出他不但爱自己的母亲,还爱着祖国和远在祖国的朋友。在那之后,他写了一篇名叫《寻梦》的文章,表达了他热爱两个母亲的情感。
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我一定要向季羡林学习。我有时对母亲发脾气;有时还偷懒,没有更努力地学习。而他从小失去了母亲,得不到母亲的呵护,却没有受影响,反而更加热爱、思念母亲,更加勤奋学习,考取了博士学位,并去德国留学。在哥廷根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母亲。在《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一生最大的悔,就是没能孝敬母亲。”这样一位大学者,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最后悔的竟然是没能孝敬母亲,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在生活中要向季羡林学习,从小孝敬母亲,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她泡一杯热茶、拿一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能作一些复杂的家务了。不然,如果她像作者的母亲一样早逝,再想孝敬她也没时间了。
贵州黔西南兴义市红星路小学六年级:王宇晨
季羡林日记 篇2
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曾用名李长植,山东利津人。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今属临清)人。两人是同乡,是刚上小学就认识的同学。但不久因为季转学而分开了。小学和中学两人都在济南,却不在一个学校。李长之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改入哲学系);前一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语系,这样又成为清华同学,且是相交甚好的朋友。季羡林说:“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当时并没有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追忆李长之》)
李长之这时已经是崭露头角的文艺批评家。他与当时任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合聘教授的郑振铎早就熟悉,李长之十二三岁时就有诗作发表在《儿童世界》,杂志的编者就是郑振铎。于是,“四剑客”都拜在郑振铎先生的门下。他们曾到郑先生燕京大学的住宅拜访过,郑藏书插架之丰富,让年轻人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1933年,郑振铎和巴金、靳以等筹备《文学季刊》,延揽南北文化精英。李长之、林庚进了编委会,吴组缃、季羡林成为特约撰稿人。创刊号1934年1月1日出版,印在杂志封面上的“本期执笔人”中就有他们的名字。这四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心里确实有点飘飘然的欣喜。第一期刊登的有李长之的论文《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翻译的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关于老舍《离婚》的书评,有吴组缃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季羡林评丁玲《夜会》的书评《夜会》。
《文学季刊》第一期售罄之后,迅疾再版。但再版时巴金抽掉了季羡林的评论文章、部分广告和封底编委会及特约撰稿人名单。
李长之负责刊物的书评,季羡林的文章是他邀约,并经过编委会同意发排的。但现在撤销,并没有经过编委会同意,李长之也不知道,他当然是不满意的。郑振铎与朱自清也认为巴金的做法欠妥。
这些80年前的旧事,早如过眼烟云随风飘逝,但有意思的是,几经战乱兵火,季羡林的一本日记(1932年8月22日―1934年8月11日)却留了下来。日记中恰好有与《文学季刊》以及下文将要说到的《文学评论》有关的记录。这本日记在季羡林生前已经一字不改地公开出版,书名就叫《清华园日记》(以下日记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934年3月25日日记:“这几天心里很不高兴――《文学季刊》再版竟然把我的稿子抽了去。不错,我的确不满意这一篇,而且看了这篇也很难过,但不经自己的许可,别人总不能乱抽的。难过的还不只因为这个,里面还有长之的关系。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起他们呢?”第二天的日记又记:“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
当年的李长之、季羡林都年轻气盛,社会历练不足,说点气话是自然的。但接下来李与巴的龃龉又有发展,李长之说:“巴金先生自发表了批评文字可以包花生米的论调以后,便妄测我在报上有文字攻击他了,终日疑神疑鬼,并唆使他的一群神经过敏而又热诚的朋友们来以明枪暗箭相压迫了。”(《〈鲁迅批判〉序》)李长之于是愤而退出《文学季刊》编委会,不再合作。这是4月间的事情。
这也算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小小的公案。当时上海《十日谈》第37期介绍李长之的短文中就说:“清华文人少壮派退出《文学季刊》,另组《文学评论》,李君即其中坚。”(小岚:《李长之》)不过,这样说并不准确。李长之退出《文学季刊》是事实,但要办《文学评论》的打算早在1932年就已经开始酝酿。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记录了《文学评论》从开始筹办至出版的前前后后:
最早是1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昨天长之同我谈到,要想出一个刊物,名《创作与批评》,自己出钱,以他、我、张文华为基本。他说中国文学现在缺乏主潮,要在这方面提醒别人。我非常赞成。”
接下来,1933年中有多次同长之(有时林庚也在场)商谈的记录。
转眼之间就到了1934年,3月3日日记:“先到露薇处。同长之我们三人谈了半天关于文学评论(我们几个人办的)的事情。关于特别撰稿人、编辑各方面的事情都谈到了,不过唯一问题就是出版处。我们拿不出钱来,只好等看郑振铎交涉得如何――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还在吹着肥皂泡。不过这泡却吹得很大。我们想把它作为中德学会的鼓吹机关,有一鸣惊人的气概。但是这泡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现在还不敢说。无论怎样,年轻人多吹几次肥皂泡,而且还是大的,总归是不坏的。”
3月29日,《文学季刊》抽去文章之后,季羡林办刊物的心愿更为迫切:“同露薇、长之又谈到出版一个杂志的事情。我现在更觉到自己有办一个刊物的必要,我的确觉得近来太受人侮辱了,非出气不行。”但是也不想过分张扬,4月4日:“前几天另外一页上露薇作了一个消息,说到《文学评论》要出版,对《文学季刊》颇为不敬,说其中多为丑怪论(如巴金反对批评)。这很不好,本来《文学评论》早就想出,一直没能成事实。最近因为抽我的稿子和不登长之的稿子,同郑振铎颇有点别扭,正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消息,显然同《文学季刊》对立,未免有悻悻然小人之态,而且里面又有郑振铎的名字,对郑与巴金的感情颇有不利。昨晚长之去找郑据说结果不很好。”
日记中季羡林也记下自己的不愉快,或因刊物的宗旨确定,或因个人的进退得失。4月21日:“长之约我进城,因为今晚文学评论社请大学出版社社长吃饭,讨论印刷问题。”“文学评论社及特约撰稿人的信,代表人没写我的名字,非常不高兴,对这刊物也灰心了。这表示朋友看不起我。”5月2日:“对《文学评论》虽然因为长之的热心也变得热心了一点,但晚上看张露薇那样愚昧固执的态度又不禁心凉了。行将见这刊物办得非驴非马,不左不右,不流氓不绅士,正像张露薇那样一个浑身撒着香水穿着大红大绿的人物。”5月9日:“《文学评论》前途不甚乐观,经费及各方面都发生问题,办一个刊物真不容易。因为种种原因,我对这刊物也真冷淡,写代表人不写我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我为什么拼命替别人办事呢?”5月28日:“我们的《文学评论》到现在仍在犹疑中,今天你赞成出,我不赞成;明天我赞成,你不赞成,犹犹疑疑了,莫知所措――地地道道的一群秀才,为什么自己连这点决断力都没有呢?”
牢骚尽管发,工作照样做。计划在5月15日出版的第一期,结果因为印刷上的问题,从6月到7月,从济南到北平,几经折腾,杂志出版时已经是8月1日了。大功告成,季羡林这天的日记满纸喜悦:“今天早八点同长之进城。先到大成,《文学评论》已经装订好了,居然出版了,真高兴,印刷装订大体都满意。”
《文学评论》的《发刊词》说:
我们认为文学是种学问,这就是说需要研究,凡武断和模糊,我们是杜绝的;我们又认为文学是种事业,这就是说我们愿意拿出全副精神来去从事,而我们的趣味乃是在事业本身,因而任何暂时的困阻,毁誉,利害,都不足动摇我们的决心及志愿。
在理论上,我们依了文艺科学(Literarwissenschaft)的内容,有我们的三大目标,从文艺创作之根本的原理原则,建设文艺美学(Literarasthetik),以文艺美学的应用,而致力于文艺批评(Literkritik),又以文艺批评的应用,贡献为文艺教育(Literarpagogik)。依了近代的研究精神,我们的方法,将是综合的,系统的,出发自文化的全般和整个的,而不是支离的,部分的,只见其为树而忘其为林的;我们的观点是科学的,是集团的,而不是神秘的,个人的。
和理论兼重,我们重货色。文学(Literartur)是时代的,但文学之上,还有纯文艺(Dichtung),却是永久的。理论的对象是二者,创作的对象,也没有两样。
我们始终的态度,将是三个:不偏于“社会”而忽略“人”,不重于“物质”,而轻视“精神”,所以,第一,我们愿意是康健的;儿嬉是我们所不屑,胡闹是我们所不肯,消闲是我们所不忍,所以,第二,我们愿意是严肃的;尽管有的刊物是为的“党”,为的“派”,为的“帮”,但我们认为文化学术是人类的,所以,第三,我们愿意是公正的。
《文学评论》以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为主,同时刊登作品和外国名著的译文。西谛(郑振铎)的文学评论《绅士和流氓》,登在第一期首页。李长之有多篇评论,其中《文坛上的党派》一文末句是:“要文坛有希望么,先须冲开这些乌烟瘴气的派和党!”可见余怒未息。文学作品中有林庚的诗、季羡林的散文和李广田、卞之琳、董秋芳、徐霞村、侍桁等的创作或翻译。杂志为16开本,双月刊,10月出了第二期后因为没有财力支撑就停刊了。
杂志版权页编辑人中除李长之以外,另有一人是杨丙辰。
杨丙辰(1896―?),原名杨震文,字丙辰。河南南阳人。1917年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一生致力于德国文学译述,以及德国文化研究。他引领李长之走上学习德国古典美学的道路。李长之1934年写有近两万字的长文《杨丙辰先生论》,叙述与杨先生相识、相处、相知的过程,对杨极为尊敬。季羡林说:“我同长之还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兼任教授杨丙辰先生。他也是冯至先生的老师。”与李长之不同,季羡林认为:“杨先生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追忆李长之》)杨死于“文革”的暴风雨中。张中行有《杨丙辰》一文,留下了这位悲剧人物朴厚而又迂阔的几个片断。
季羡林日记 篇3
打字情缘
在季羡林住的那条街上,有一个叫迈耶的德国人。迈耶先生是一个小职员,为人憨厚朴实,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他更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
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拜访田德望,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几岁,年轻英俊,身材高大,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喜欢上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但是,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产生恋情,还有另外一段因缘。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稿子因为反复修改,很乱,打字量也很大。恰巧伊姆加德小姐会打字,而且她家里有打字机,并表示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十分专业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读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他们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羡林才摸黑回家。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待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出来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他还经常去迈耶家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字。
日久生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就连迈耶太太也看出来了。后来,迈耶家凡有喜庆的事,招待客人吃点心,喝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季羡林和伊姆加德还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两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谈,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见面,两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丽的容貌、悦耳的声音、迷人的笑容,使季羡林怦然心动,每次见到她,都感到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季羡林初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觉。同样,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对季羡林的爱慕之情。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心扉,让自己的激情喷涌出来,和伊姆加德继续相爱直到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身。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离开伊姆加德。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会慢慢地忘记自己。
季羡林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季羡林咽下这个苦果,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悲情往事
1991年,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首次披露了他50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他在《留德十年・迈耶一家》中写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像。
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吃过晚饭,7时30分到迈耶家去,同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回到家,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时,我到迈耶家,把稿子打完。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才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信。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活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
然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季羡林日记 篇4
《怀念母亲》一文就充分显示了季老对两位母亲的想念与眷恋,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情感,季老用摘录自己在哥廷根时记下的日记的方式,将自己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浓烈的怀念母亲和祖国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季老在异国他乡留学期间,每天对母亲的想念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日记不仅记录了季老“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的魂牵梦绕之情,也成为他倾诉感情的载体。通过几则短短的日记摘录,我们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季老诚挚的怀念母亲、热爱祖国的情怀,给读者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
从文中我们不仅能够读出季老对母亲炽热的情感,还能够感受到他良好的记日记的习惯。从学生时代开始,季老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的经历和情感在日记中得到了永恒。他这样表述日记的价值:“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
其实,不仅季老有良好的记日记的习惯,很多名人大家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生前每天坚持写日记,不管工作和写作有多忙,二十余年的日记写作从未间断过。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坚持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直至逝世前四天。他曾对来访者说:“这些作品的写作,全得益于平日的日记资料,否则,我不知道材料在哪里,要多费时费力才能写出作品啊!”他也曾告诫后生晚辈:“要多读多写多观察,特别要多写观察日记,这是写作的基本功。”
通过这些名人的事例,相信每位同学都能感受到写日记的诸多益处,写日记不仅可以将自己生活中很多值得记录的东西记下来,为写好作文积累素材;还能提高人的观察、写作能力,让你不再为写作文感到困难;写日记还能帮你养成思考分析的习惯,使人明辨是非,提高修养。当然,通过写日记还可以把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情感永久地保存下来,让美好的记忆得到珍藏。